对话王中林院士:青年研究者想做出0-1的创新,要瞄准一个方向,锁定目标,长期坚持

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 王中林
出品|搜狐科技
作者|周锦童
9月9日,“新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发布会”能源技术专场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会上发布了海洋蓝色能源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退役新能源组件的热解处置技术和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系统三项能源技术成果。
海洋蕴藏着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全球波浪能理论总量高达数太瓦。然而,如何高效捕获低频、不规则的海洋能量,一直是技术瓶颈。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发布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技术,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方案。
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王中林表示:“海洋是地球能源的终极宝库,但海洋能具有频率低、分布广和环境复杂等特点,制约了其大规模开发,我们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技术,创新性地实现了对低频波浪能的高效俘获,结构简单、环境适应性强、材料成本相对低廉。”
据王中林透露,基于该技术研制的首台套发电部分体积为1立方米的海洋浮标样机,已在海上示范运行,为海洋物联网设备、环境监测浮标等提供稳定电力。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等设备的“退役潮”即将到来。预计到2030年,全国年退役量将突破500万吨。华北电力大学陆强教授团队研发了退役新能源组件绝氧热解处置技术,助力实现这些组件的绿色、高效、高值化回收。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新能源发电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陆强
展开全文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新能源发电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陆强在会上分享了最新进展:“目前,我们设计的退役新能源组件热解系统已经在全国十余个省份得到广泛应用,我们成功实现了年处理数万吨退役新能源组件的目标,验证了技术的工程稳定性和经济性。”
第三项技术是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系统,依托全球先进的多级降尺度区域气象大模型技术,将场站级气象预测准确率提升了15%,风电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了10%。

深圳能源集团智慧能源领域首席专家 陈正建
深圳能源集团智慧能源领域首席专家陈正建表示,该系统通过减少预测偏差带来的弃风、弃光现象,优化发电计划排产,有效提升了电网对波动性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智慧之眼”。
会后,围绕这三项重要成果,搜狐科技等媒体对话了发布嘉宾,听他们分享最新技术进展和应用前景。
以下为此次对话精编:
媒体:纳米摩擦发电技术跟海上风电或者跟光伏相比,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王中林:海上风电和光伏技术发展相对成熟,但光伏是有光才有伏,有光才有电。它可以白天发电,晚上不一定。天气好可以,天气不好就不可以,昼夜分明;风一般在海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海上风电现在发展很快,但也有不确定性。
摩擦纳米发电技术是原理上的新发现,是收集低品质低幅度能量的一个底层技术。在海上的话,水总是在流动,那么对这种微动,把它变成电力或者电信号历来很难,有能源但是不可用。所以要把这不可用的、分布广、密度低的高熵能源用起来,就要靠我们的发明。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技术有一定的优势。
解决能源问题不是一种技术就能完成。单一光伏也解决不了,单一风能也解决不了。只有几种技术配合起来,方能解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新能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那么稳定,所以并网也一定会有局限性。
但我们思维可以改变,并不是所有的能源都必须并网,我们一定要在当地产生、当地用,这个场景就多了。所以我们既有并网也有分布式,两个结合起来解决我们未来能源问题。所以各有优缺点,兼蓄并用方能解决我们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媒体:该技术距离真正的规模化的应用还有多远?未来3到5年内的产业化路径的挑战有哪些?
王中林:为了规模化应用我们分几步走。第一步先把这基本样机做好,就像做光伏板,我先把那个硅片做好,做好它就是基本单元,然后集成,现在我们达到了。第二步是规模化,决定于我们有多少财力投入进去。第三步是系统集成,把它集成起来以后,我觉得三年之内就能用,五年之内集成后的规模化也能实现。
最难的就是前面的样机。因为样机包含各方方面面的技术,能源回收、能源管理、能源储存等,还要实现一体化。把这个路打通了以后,我们就复制,复制以后怎么把它连接起来,相对来说挑战不是那么大,但是每一步也都是有挑战的。比如放到海里,在海里这个东西怎么能够适应?一到水里面以后,它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大量的试验,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还要不断的把这个集成起来,能够系统的,和大海的状况结合在一起。
搜狐科技:您对那些希望从0到1做出创新工作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王中林:我们经常讲从0到1,有大也有小。大家要想的突破是多大的突破?对于我们的这个突破来说,算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带着团队做,从开始摸索到现在20年了,这个月的20年前,我首次提出纳米发电机这个概念。这个经历,也是大团队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前期。后期发展更快了,很多的企业已经孵化出去了。
首先对年轻人提出的,就是要瞄准一个方向。因为你要看上一件大的事情,别人也看上了,都认为这个路越走越宽,那就有别人在前面走。选定后要锁定这个目标,不要因为事小而不为。大事你想做,谁都想做,我们把小事做成大事,把一个看着不重要的研究持续做下去,最后全世界一片都在跟着做。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定力。
最重要是要坚持,创新工作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就能做出来的,是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努力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到现在我们基础理论、基本技术,这个工程样机都在方方面面地开发出来了,下一步就是产业化,我相信我们团队下面几年发展会更好。
年轻人不要急于求成,大成果都不是一天干出来的/1839年法国科学家就发现了光伏现象,1905年爱因斯坦用光量子解释了什么叫光电效应。1954年才有第一个这么大的硅基光伏片。到1977年光伏发电,当时的价格是77美元一度电,到现在是几美分一度电,整个发展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科学家们干了什么呢?把技术的方方面面打通,优化材料的成本,才有今天的光伏发电。
创新工作是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也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我们争取一代人能完成。我们现在是摘取了科技发展的红利,但在前期的科技发展我们并没有做太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做原创的0到1的研究,对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挑战。未来能不能自强自立?未来能不能在科技上引领世界的发展?我们有没有这种志向?有没有这种大思路?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
媒体:热解技术在处理不同种类的退役组件时,如何实现标准化问题?
陆强:我们的标准是对某一种单一的退役组件,但对不同类型的退役组件的话,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退役下来的风机叶片是五六十米一根,现在最大的风机叶片已经可以做到接近200米。为了运输方便的话会简单切一切。但不能切的太碎,叶片里面有纤维,如果把它切的太短的话,纤维也被切短了,就不值钱了。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一般都要做大尺寸的叶片。比如说我们这边风机叶片,可以1米到2米一段,那么直接进去做热解。光伏组件也一样,它是一个三明治结构,上面一层玻璃,下面一层背板,最中间是晶硅电池片,在玻璃、晶硅电池片、背板中间填充的都是胶。这个玻璃如果是一套完整的,就会比碎的玻璃相对更值钱。
对于风机叶片,光伏组件和锂电池,它这个设备结构是不一样的。叶片和那个光伏都需要做大尺寸,这个电池是可以直接做小尺寸。另外,它的原料、产品也不一样,所以它们对应的工艺截然不同。我们可以针对风机叶片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产品,针对光伏组件也做成了标准化产品,锂电池也是同样的处理,但设备是截然不同。
搜狐科技:与传统的焚烧或者填埋相比,热解工艺在碳排放和污染控制方面有哪些优势?在处置过程中怎么高效分离回收高价值的材料,避免有毒物质的释放?
陆强:我们的工艺是绿色低碳,如果把风机叶片直接填埋,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地向环境中释放出二氧化碳或甲烷。如果去焚烧风机叶片的话,以填埋作为基准的话,它也是有碳减排的。
如果以焚烧为基准的话,因为焚烧过程中会释放热量,我们可以简单认为它能够替代一部分的煤,那么它就能够有一定的碳减排功能。
比如一吨叶片产生的热量可以替代半吨煤,那每处理1吨叶片,就能够节省半吨以上的煤。我们的热解是回收了它里面的有机物,都变成了油和气,把里面的无机物纤维等组分都给回收回来。
纤维是工业制造的,一定是耗掉很多能源的。纤维制作过程需要拉丝,如果没有能源,纤维拉丝就无法实现,我们把纤维回收回来,就替代了传统的工业纤维,不需要再去造新的纤维了。我们的碳减排效果非常的好,一吨风机叶片的热解处置回收,大约能够有2.7吨的二氧化碳减排。
从回收来说,所有的新能源器件都是一个非常致密的结构,油盐不进。但热解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机物高温下才会分解,无机物是不变的。像电池片,它是一种叫做EVA的胶膜,非常的紧密,想渗透进去都渗透不进去。我们用热解一加热,胶膜就失效了,玻璃和电池片就自动分开了,我们一边得到玻璃,一边得到电池片。
器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污染元素,比如光伏组件它里面最下一层叫含氟背板,处理过程中一定有氟会释放出来。在热解的过程中,氟跑出来了,而我们会把氟全都焚烧,焚烧后,所有的有机氟都会变成氟化氢,把它回收回来,还能直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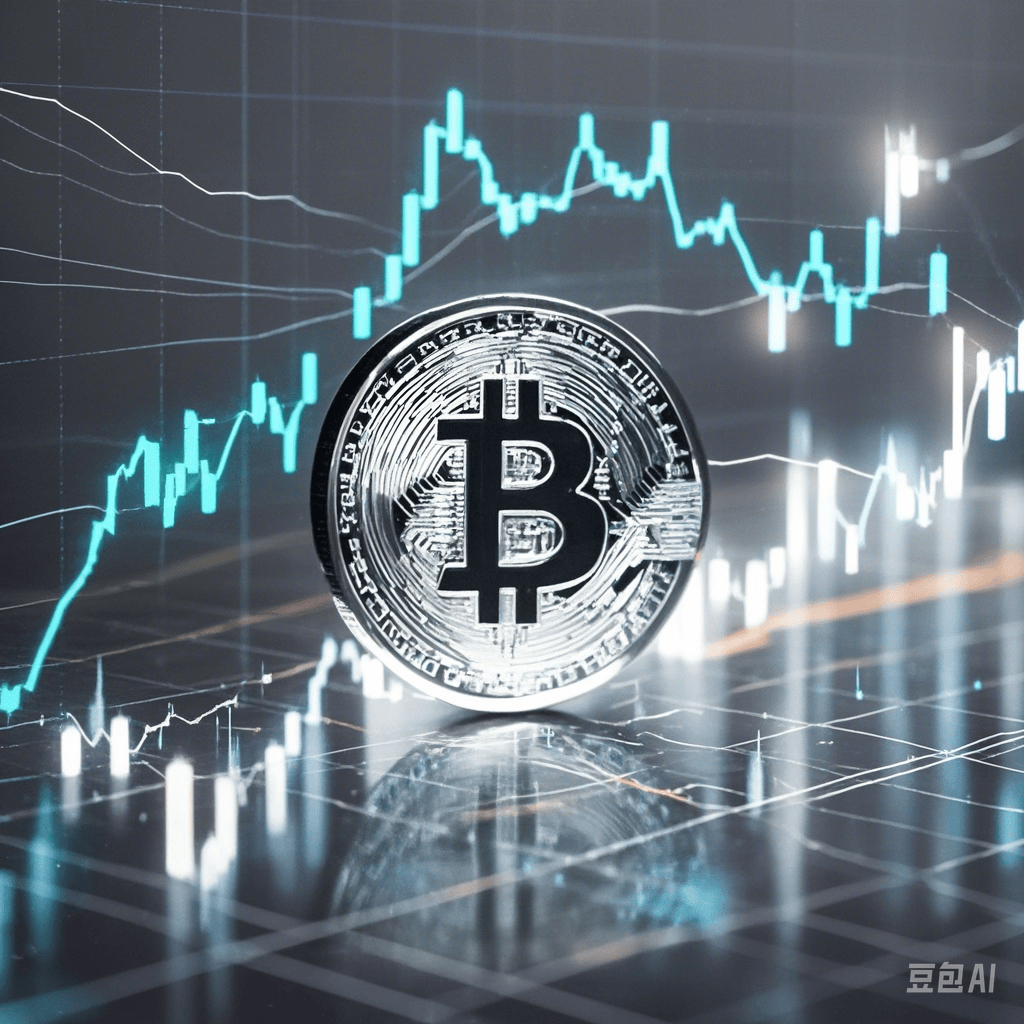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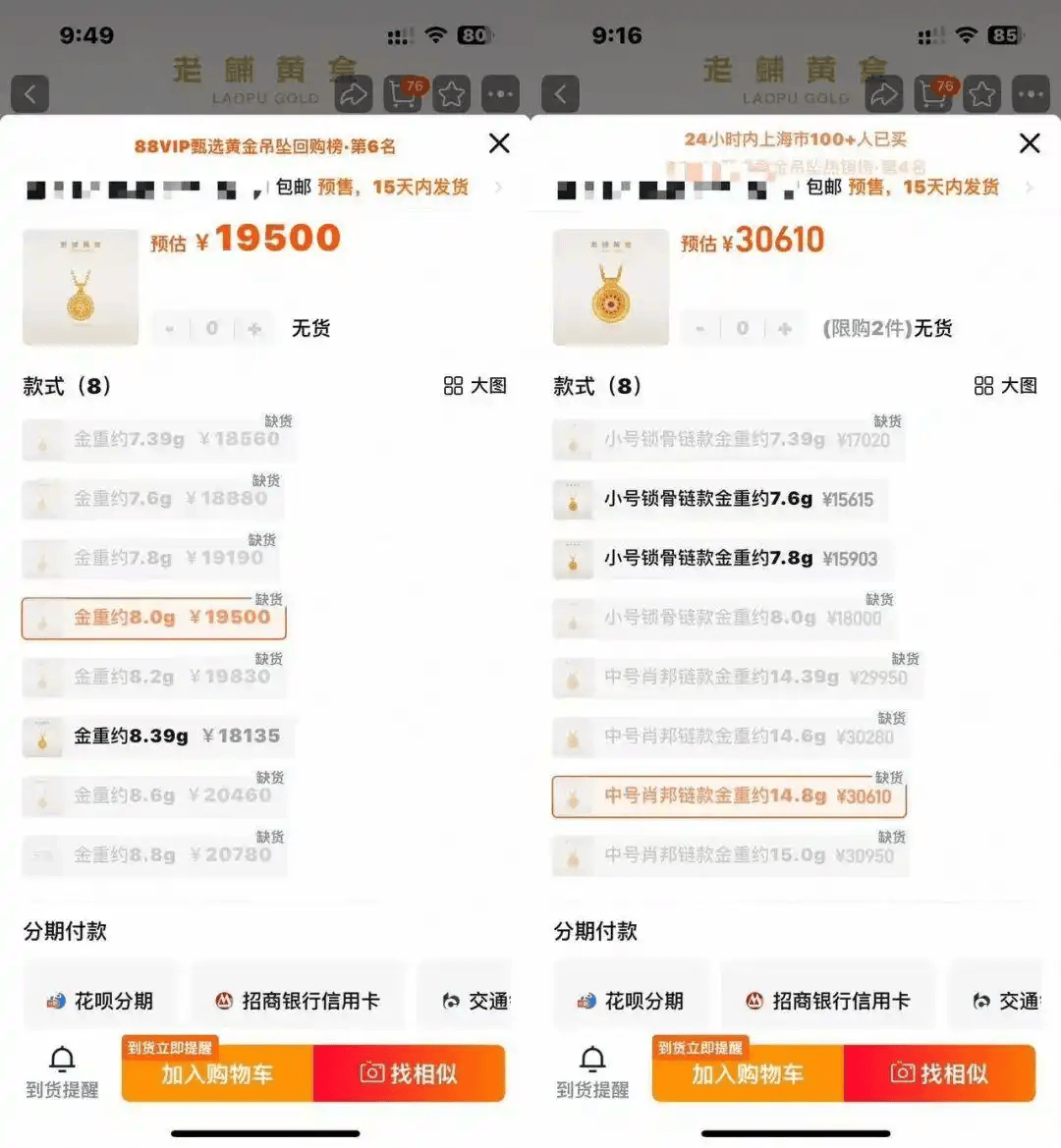

评论